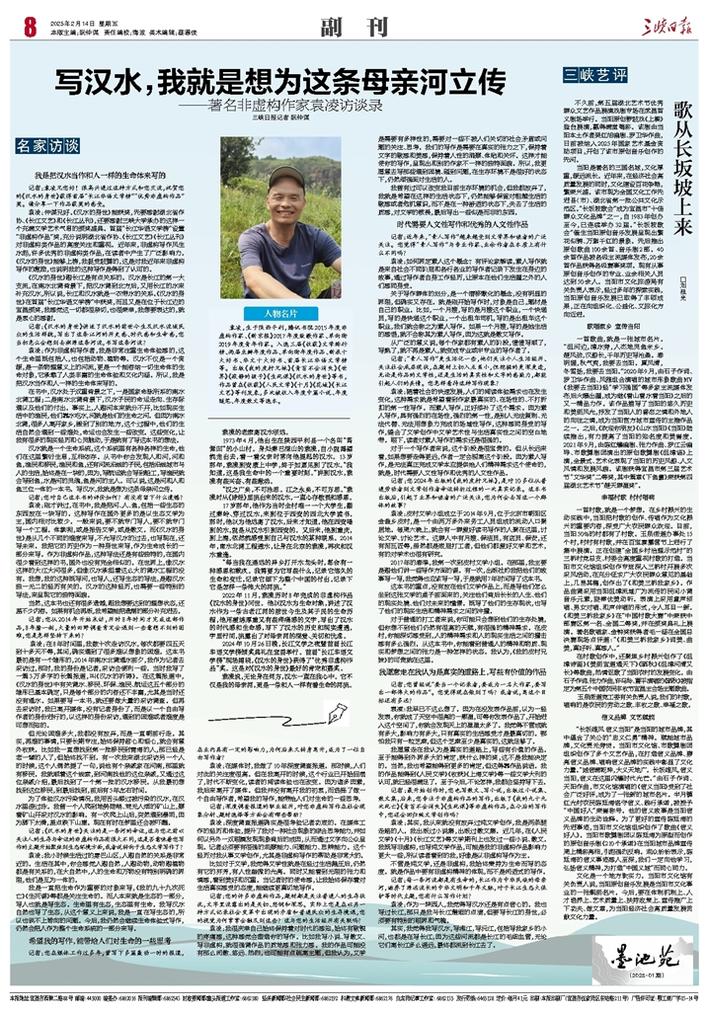三峡日报记者 阮仲谋
人物名片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腾讯书院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两届豆瓣年度作品、单向街年度作品、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等。出版《我的皮村兄妹》《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生死课》《汉水的身世》等书,作品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花城》《长江文艺》等刊发表,多次被收入年度中篇小说、年度随笔、年度散文等选本。
袁凌的老家离汉水很远。
1973年4月,他出生在陕西平利县一个名叫“筲箕凹”的小山村。身处秦巴深山的袁凌,自小就渴望能走出去,看一看父亲时常向他提起的汉水。13岁那年,袁凌到安康上中学,终于如愿见到了汉水。“我知道,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讲到汉水,袁凌有些兴奋、有些激动。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袁凌对从《诗经》里流出来的汉水,一直心存敬畏和感恩。
17岁那年,他作为当时全村唯一一个大学生,翻过秦岭、穿过汉水,来到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读书。那时,他以为他远离了汉水,后来才知道,他在西安喝到的水,就是从汉水引到西安的。又后来,他到重庆,到上海,依然能感受到自己与汉水的某种联系。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通水,让身在北京的袁凌,再次和汉水重逢。
“每当我在遥远的异乡打开水龙头时,都会有一种感恩和歉疚。我需要为它写些什么,记录它悠久的生命和变迁,记录它眼下为整个中国的付出,记录下它是怎样一条伟大的河流。”
2022年11月,袁凌历时8年完成的非虚构作品《汉水的身世》问世。他以汉水为生命对象,讲述了汉水作为一条古老江河的前世今生及其子民的生命历程,他用凝练厚重又有些疼痛感的文字,写出了汉水的时代感和生命感,写下了汉水的历史和现实遭遇,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母亲河的深爱、关切和忧虑。
2024年10月26日晚,长江文学之夜暨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颁奖典礼在宜昌举行。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现场揭晓,《汉水的身世》获得了“优秀非虚构作品”奖。这是对《汉水的身世》最好的肯定和嘉奖。
袁凌说,无论身在何方,汉水一直在我心中。它不仅是我的母亲河,更是一条和人一样有着生命的河流。
名家访谈
我是把汉水当作和人一样的生命体来写的
记者:袁凌兄您好!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和您交流,祝贺您的《汉水的身世》获得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优秀非虚构作品”奖。请分享一下作品获奖的感受。
袁凌:仲谋兄好。《汉水的身世》能获奖,先要感谢湖北省作协、《长江文艺》和《长江丛刊》,还要感谢三峡大学承办的这样一个充满文学艺术气息的颁奖盛典。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设置“非虚构作品”奖,充分说明湖北省作协、《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对非虚构类作品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近年来,非虚构写作风生水起,许多优秀的非虚构类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力。《汉水的身世》能够上榜,我挺受鼓舞的,这是对我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激励,也说明我的这种写作是得到了认可的。
《汉水的身世》跟长江是有点关系的。汉水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在南水北调背景下,把汉水调到北方后,又用长江的水来补充汉水,所以说,长江和汉水就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汉水的身世》在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中获奖,而且又是在位于长江边的宜昌颁奖,我感觉这一切都很亲切,也很荣幸,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衷心的感谢。
记者:《汉水的身世》讲述了汉水的前世今生及汉水流域民众的生活样貌,写出了这条江河的历史感、时代感和生命感,您当初怎么会想到去溯源这条河流,书写这条河流?
袁凌:作为非虚构写作者,我是非常注重生命体验感的,这个生命里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植物等。汉水不仅是一个资源,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个能容纳一切生命体的生命对象,它承载了人类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内涵。所以,我是把汉水当作和人一样的生命体来写的。
在书中,汉水处于双重背景之下,一是国家命脉所系的南水北调工程;二是南水北调背景下,汉水子民的命运走向、生存际遇以及他们的付出。事实上,人跟河本来就分不开,比如现实生活中的渔民,他们靠水吃水,河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河。但因为南水北调,很多人离开家乡,搬到了别的地方,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生活自然会遇到一些难处,命运也会发生一些改变。这些变化,让我有很多的现实经历和心灵触动,于是就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汉水就是一个生命系统,这个系统里有各种各样的生命,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互相依存。从书中你会发现人和河,河和鱼,渔民和移民,渔民和鱼,还有河流沿线的子民,包括沿线城市与人的生活,始终是在一块的,因为,写航运就会写到船工,写渔民就会写到鱼,水是河的灵魂,鱼是河的主人。可以说,这是河和人和鱼三位一体的一本书。写汉水,我就是想为这条母亲河立传。
记者:您对自己这本书的评价如何?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袁凌:刚才讲过,在书中,我是把河、人、鱼,包括一些生态的东西放在一块写的。这种写作在国外更多的是以生态文学为主,国内相对比较少。一般来说,要不就专门写人,要不就专门写一个工程。体裁呢,或是报告文学,或是散文。而《汉水的身世》是从几个不同的维度来写,不光写汉水的过去,也写现在,还写未来。我把它的历史作为一种身世来写,作为生命成长的一部分来写。作为非虚构作品,这种写法还是有些独特的,在国内很少看到这样的书,国外也没有完全相似的。在世界上,像汉水这样的大江大河很多,但像汉水承担着这么大的调水工程的没有。我想,我的这种既写河,也写人,还写生态的写法,是跟汉水独一无二的经历有关的。汉水的这种经历,也需要一些特别的写法,来呈现它的独特面貌。
当然,这本书也还有很多遗憾,距我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还差不少内容。如果有机会再版,我希望能把遗漏的部分补充进去。
记者:您从2014年开始采访,历时8年时间才完成这部作品,8年磨一剑,大量的田野调查肯定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袁凌:在8年时间里,我数十次走访汉水,每次都要四五天到十多天不等,其间,确实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本书最初是有一个雏形的,2014年南水北调通水前夕,我作为记者去采访过,那时,我的身份是记者,采访会便利一些。当时我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长篇报道,叫《汉水的祈祷》。在这篇报道中,《汉水的身世》中有关调水、移民、环保、渔民、航运这五个部分的雏形已基本确定,只是每个部分的内容还不丰富,尤其是当时还没有通水。如果要写一本书,就还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但再去采访时,我已离开媒体,没有记者身份了,而是以一个自由写作者的身份进行的,以这样的身份采访,遇到的困难或者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无论困难多大,我都没有放弃,而是一直朝前行走。其实,再难的事情,只要长期专注,始终保持耐心和恒心,就会有意外收获。比如我一直想找到第一批移民到青海的人,那已经是老一辈的人了,但始终找不到。有一次我来湖北采访另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偶然提了一句,说他有个亲戚家在河南,那里就有移民。我就顺着这个线索,到河南找他的这位亲戚,又通过这位亲戚介绍,最后找到了一个第一批的汉水移民。从我最初想找到这位移民,到最后找到,前后有5年左右时间。
为了体验汉水污染情况,我用舌头舔过被污染的汉水,在汉水里游过泳。我曾一个人爬到地势陡峭、荒无人烟的矿山上,察看矿山开采对汉水的影响。有一次爬上山后,突然遇到暴雨,因为脚下太滑,差点跌下山崖。现在有时在梦里还会被吓醒。
记者:《汉水的身世》关注的是一条河的命运,这与您之前以关注人的生存与命运的非虚构作品有很大不同,这是否意味着您写作的主题开始聚焦到生态环境方面,或者说转向于生态文学写作了?
袁凌:我小时候生活过的秦巴山区,人跟自然的关系是非常近的。生活在其中,你会感觉人跟自然,人跟动物,动物跟植物都是有关系的,在大自然中,人的生命和万物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他们是互为一体的。
我是一直把生命作为重要的对象来写,《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生死课》等都是关注生命的。而人本来就是生态的一部分,写人也就是写生态。生命里有生态,生态里有生命。我写汉水自然也写了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一直在写生态的,所以也谈不上转向的问题。今后,我仍然会继续生命体验式写作,仍然会把人作为整个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来写。
希望我的写作,能带给人们对生命的一些思考
记者:您在媒体工作过多年,曾写下多篇轰动一时的报道,在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为何后来又转身离开,成为了一位自由写作者?
袁凌:在媒体时,我做了10年深度调查报道。那时候,人们对此的关注度很高。但在我离开的时候,这个行业已开始回落了,时代不断变化,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在改变。因为诸多因素,我后来离开了媒体。但我并没有离开我的初衷,而选择了做一个自由写作者,希望我的写作,能带给人们对生命的一些思考。
记者:深度调查报道的职业经历,对您非虚构写作在社会现象分析、题材选择等方面会有哪些帮助?
袁凌:深度调查报道确实是很考验记者功底的。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和体验,提升了我对一种社会现象的综合思考能力,并如何以另外一双眼睛发现现象背后的成因,从而通过文字向公众呈现。记者必须要有很强的观察能力、问题能力、思辨能力。这个经历对我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比如对于文学,我觉得文学性就是在经过生活碾压后,仍然有它的芬芳,有人性幽微的光亮。同时又能看到无限的张力和情感,看到美好和沉重。当记者时的使命感,让我始终保存着对生活真实感受的态度,能继续更真切地写作。
记者:您的许多非虚构作品,题材都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文字里流露出的是关切、悲悯和深思。实际上您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记录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矛盾和普通民众的生存境遇,您的视觉为何常常会触及到这些?这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联吗?
袁凌:我很庆幸自己始终保持着对时代的感知,始终有敏锐的疼痛感,这种感觉会塑造你的写作。比如我写小说、写散文、写非虚构,就很强调作品的质地感和张力感。我的作品可能没有那么闲散、悠远、热烈,也可能有点疏离主题,但我认为,文学是需要有多样性的,需要对一些不被人们关切的社会矛盾或问题的关注、思考。我们的写作是需要在真实的张力之下,保持着文字的敏感和美感,保持着人性的洞察、体贴和关怀。这样才能使你的写作,呈现出和别的作家不一样的独特面貌。所以,我更愿意去写那些遇到困境、碰到问题,在生存环境不是很好的状态下,仍然顽强面对生活的人。
我曾有过可以改变我目前生存环境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我就是希望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仍然能够保留对粗糙生活的敏感或者危机意识,而不是在一种舒适的状态下,失去了生活的质感,对文学的敬畏,最后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时代需要人文性写作和优秀的人文性作品
记者:近年来,“素人写作”越来越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您觉得“素人写作”与专业作家、业余作者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
袁凌:如何界定素人这个概念?有评论家解读,素人写作就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和各行各业的写作者记录下发生在身边的故事,通过写作者自身工作经历,让原本在他们生活圈之外的人们感同身受。
关于写作群体的划分,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概念,没有明显的界限,但确实又存在。就是刚开始写作时,对象是自己,题材是自己的职业。比如,一个月嫂,写的是月嫂这个职业,一个快递员,写的是快递这个职业,一个出租车司机,写的是出租车这个职业,我们就会称之为素人写作。如果一个月嫂,写的是她生活的感悟,就不会称其为素人写作,因为这就是散文写作。
从广泛的意义说,每个作家都有素人的阶段,慢慢写顺了,写熟了,就不再是素人,就变成专业或半专业的写作者了。
记者:“素人写作”更生活化一些,他们关注个人生活经历、关注社会底层现状,在题材上切入点虽小,但挖掘的更深更透,无论是作品的文学性,还是生活的真实性和文字的感染力,都能引起人们的共情。您怎样看待这种写作现象?
袁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阅读体验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需求就是希望看到作家最真实的、在场性的、不打折扣的第一性写作。而素人写作,正好添补了这个需求。因为素人写作,具有强烈的在场性,强烈的第一性,是别人无法复制、无法代替、无法用想象力完成的场域性写作,这种感同身受的写作,缝合了文学创作中文学艺术性与生活真实性之间的空白地带。眼下,读者对素人写作的需求还是很强的。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个阶段是很宝贵的。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想要走得更远,作者一定会脱离这个阶段。因为素人写作,是无法真正完成文学本应提供给人们精神需求这个使命的,就是,时代需要人文性写作和优秀的人文性作品。
记者:您2024年出版的《我的皮村兄妹》,是对10多位从普通劳动者到文学创作者命运转折过程的一次真实记录。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业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您为何会去写这一个群体的故事?
袁凌:皮村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是一个由两万多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地。每周六晚上,就会有一群爱好读书写作的人聚在这里,讨论文学、讨论艺术。这群人中有月嫂、保洁员,有店员、保安,还有泥瓦匠等,虽然都是底层打工者,但他们都爱好文学和艺术,有的对学术也很有研究。
2017年的春季,我第一次到皮村文学小组。在那里,我主要是跟他们讲一些写作方面的课。有一次,出版社约我把他们的故事写一写,我觉得也应该写一写,于是就用7年时间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重点,没有放在他们文学作品上,而是写他们怎么坐到这张文学的桌子前面来的,关注他们背后长长的人生、他们的现实处境、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既写了他们的生存现状,也写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需求之间的冲撞。
对于普通的打工者来说,你可能只会想到他们的生存处境,但你想不到他们仍然有很高的天赋,有很强的精神需求。在皮村,你能深切感受到,人的精神需求和人的现实生活之间的撞击感有多么强烈。从这本书中,你能看到普通人的精神和物质、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张力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我认为,《我的皮村兄妹》的可贵就在这里。
我愿意走在我认为是真实的道路上,写些有价值的作品
记者:您曾经说“要当一个记录者,要成为一名大作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您觉得现在做到了吗?或者说,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袁凌:我早已不这么想了。因为在没发表作品前,以为一经发表,你就成了天空中很亮的一颗星,可等你发表作品了,开始进入这个空间了,你就会发现天上的星星太多了。我觉得不管成就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只有真实的生活感受才是最真切的。哪怕我只有一粒芝麻,但这个芝麻至少是真实的,这就足够了。
我愿意走在我认为是真实的道路上,写些有价值的作品。至于能得到外界多大的肯定,获什么样的奖,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当然,我也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肯定,但这得靠作品说话。我的作品能得到《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等一些文学大刊的认可,就已经很满足了。至于今后,不论怎样,我都会坚持写下去。
记者:最开始创作时,您也写散文、写小说,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后来,您专注于非虚构作品的写作,出版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生死课》等非虚构作品,在今后的写作中,您还会回归纯文学创作吗?
袁凌: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纯文学创作,我是两条腿走路的人。我出版过小说集,出版过散文集。近几年,在《人民文学》《十月》《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上也发过一些小说、散文。我既写非虚构,也写纯文学作品,可能是我的非虚构作品影响力更大一些,所以读者看到的我,好像是以非虚构写作为主。
不管是纯文学,还是非虚构,我始终秉持为生命而写的态度。就是作品中要有非虚构精神的体现,而不是闲适式的写作。
记者:每一条河流都是有生命的,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千年文脉,对于长江生态大保护等时代主题,您有什么写作计划?
袁凌:作为一陕西人,我觉得写汉水还是有点信心的。我也写过长江,那只是我与长江邂逅的点滴,但要写长江的身世,必须要有特别的眼界和气魄。
其实,我觉得我写汉水,写湘江,写沅江,包括写我家乡的小河,也都是在写长江,因为这些河流都是长江的毛细血管,无论它们离长江多么遥远,最终都流到长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