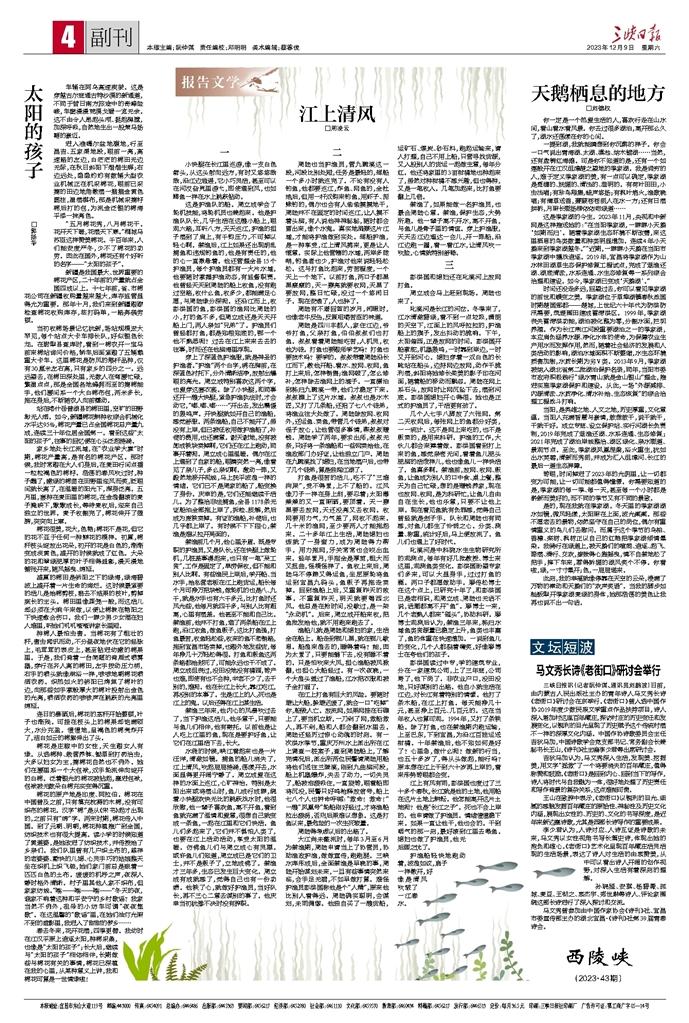□郭扬华
车辆在阿乌高速疾驶。这是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新通道,不同于昔日南方旅途中的奇峰险峻,车窗漫漫荒漠戈壁一览无余。这不由令人昂起头颅、挺起胸膛,加深呼吸,自然地生出一股策马扬鞭的豪迈。
进入准噶尔盆地腹地,行至昌吉、五家渠地段,眼前一亮,高速路的左边,白茫茫的棉田无边无际,在秋日斜阳下熠熠生辉;右边远处,隐隐约约有数辆大型农业机械正在机采棉花,眼前已采摘的田边地角散落一捆捆金黄色圆柱,星落棋布,那是机械采摘籽棉后打的包,为流金泛银的棉海平添一抹亮色。
“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桐城马苏臣这样赞美棉花。千百年来,人们能安度严冬,少不了棉花的功劳。因此在国外,棉花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太阳的孩子”。
新疆是我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二十年前的产量就占全国四成以上。十七年前,省、市棉花公司在新疆收购量越来越大,库存监管显得尤为重要。那年十月,我们来到新疆跟踪检查棉花收购库存,核打码单,一路奔袭劳顿。
当初收棉场景记忆犹新,场站规模宏大罕见,每个站点大卡车排长队,好似银色长龙。在尉犁县查库时,看到一棉农开一宝马前来棉站询问价格,轿车后面紧跟了五辆载重大卡车。这里棉花是防风的矮杆品种,仅有30厘米左右高,只有家乡的四分之一。远远望去,在棉田深处里,无数人在弯腰忙碌,繁星点点,那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摘棉能手,他们腰间系一个大白棉布包,两米多长,拖在身后,不断随农人向前蠕动。
站在喀什岳普湖县的棉田里,空旷的田野渺无人烟。如今,新疆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5%,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棉花总产量九成,连续三十年位居全国第一。看到这些“太阳的孩子”,往事的回忆便在心头泛起涟漪。
家乡地处长江流域,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棉花产量高,是有名的棉花产区。那时候,我时常跟在大人们身后,在麦田行间点播一粒粒褐色的棉籽。浩荡的春风吹过时,种子醒了,嫩绿的棉苗在田野里迎风而笑,眨眼间就长高了,在温暖的阳光下,浑身泛亮。五月里,套种在麦田里的棉花,在金浪翻滚的麦子掩映下,默默成长,等待麦收后,迎来自己独立的世界。麦子收割完了,棉花伸开了翅膀,突突向上窜。
棉花很美,花大,色艳;棉花不是花,但它的花不亚于任何一种鲜花的模样。初夏,棉秆枝头绽放出花朵,初开的花是白色的,渐渐变成淡黄色,盛开的时候就成了红色。大朵的花和翠绿肥厚的叶子相得益彰,漫天漫地铺张开来,随风摇曳、绵延。
盛夏的棉田是骄阳之下的绿海,绿海碧波上盛开着一片生命的绚烂。这时候最紧要的活儿是给棉剪枝,掐去不结果的枝叶,剪掉疯长的主头。棉田里像蒸笼一般,而这活儿却必须在大晌午来做,以便让棉株在艳阳之下快速愈合伤口。我们一群少男少女混在妇人堆里,听她们叽叽喳喳讲家长里短。
种棉人最怕虫害。当棉花有了粗壮的秆,害虫闻讯而动,不分昼夜地伏在它的经脉上,毛茸茸的表皮上,甚至钻进幼嫩的棉果里。于是,我们背着一台简陋的背厢式喷雾器,穿行在齐人高的棉田,左手按动压力柄,右手的喷头就像淋浴一样,哧哧地朝棉花喷洒农药。炽热如火的骄阳已烤焦了棉叶的边,向那些如手掌般厚大的棉叶投射出金色的光亮,喷洒农药的哧哧声在跳跃的光亮里绵延。
连日的暴晒后,棉花的茎秆开始萎顿,叶子也渐残。可挂在枝头上的棉果却饱满硕大,水分充盈。慢慢地,呈褐色的棉壳炸开了,洁白如云的棉絮伸出了头。
棉花是庄稼中的女性,天生跟女人有缘。从选棉种、栽营养钵、锄草到打药治虫,大多以妇女为主,摘棉花自然也不例外。她们在腰里系一个大包袱,双手轮流伸向绽开的白棉。泛着银光的棉花被拈起,塞进包袱,包袱被无数朵白棉充实变得沉重。
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阿拉伯。棉花在中国普及之前,只有填充枕褥的木棉,没有可织布的棉花。汉字“棉”是从《宋书》起才出现的,之前只有“绵”字。两宋时期,棉花传入中国。到了元朝、明朝,棉花种植推广到全国,纺织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读小学的时候知道了黄道婆,是她改进了纺织技术,并传授给了乡亲们。我们队里曾有几户织土布的,慈祥的老婆婆、勤快的儿媳、心灵手巧的姑娘整天坐在织机上织飞梭,她们家门前总是晾着一匹匹白色的土布。缓缓的机杼之声,夜深人静时格外清晰。村子里其他人家不织布,但家家纺线。“嗡——嗡——嗡——”冬天的夜,谁家不响着这种和平安宁的乡村歌谣?我家当然不例外,祖母的小纺车可谓“夜夜笙歌”。在这温馨的“歌谣”里,在她们油灯光照不到的暗影里,我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春去冬来,花开花落,四季更替。我幼时在江汉平原上追逐太阳,种棉采桑,也像是“太阳的孩子”;长大后,继续与“太阳的孩子”相依相伴,长期做些与棉花有关的事情,棉花已深植在我的心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和棉花可算是一世情缘啦!